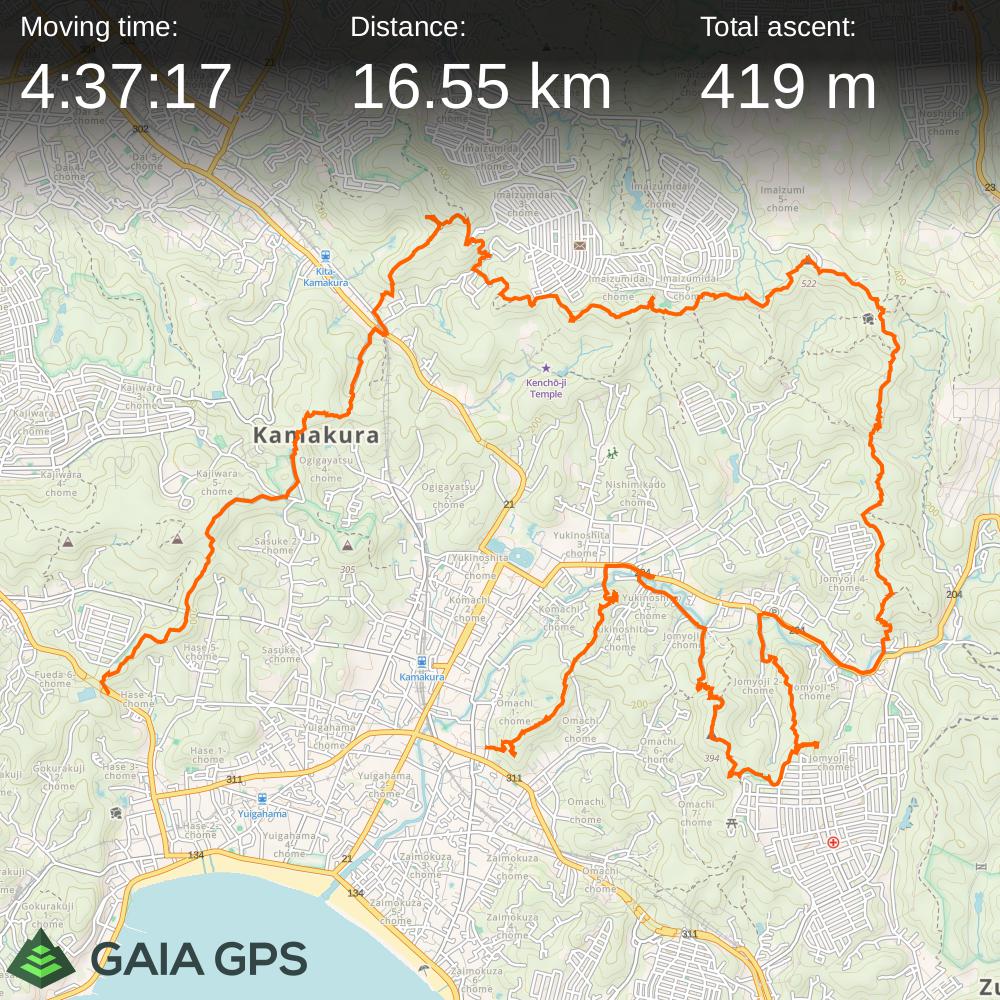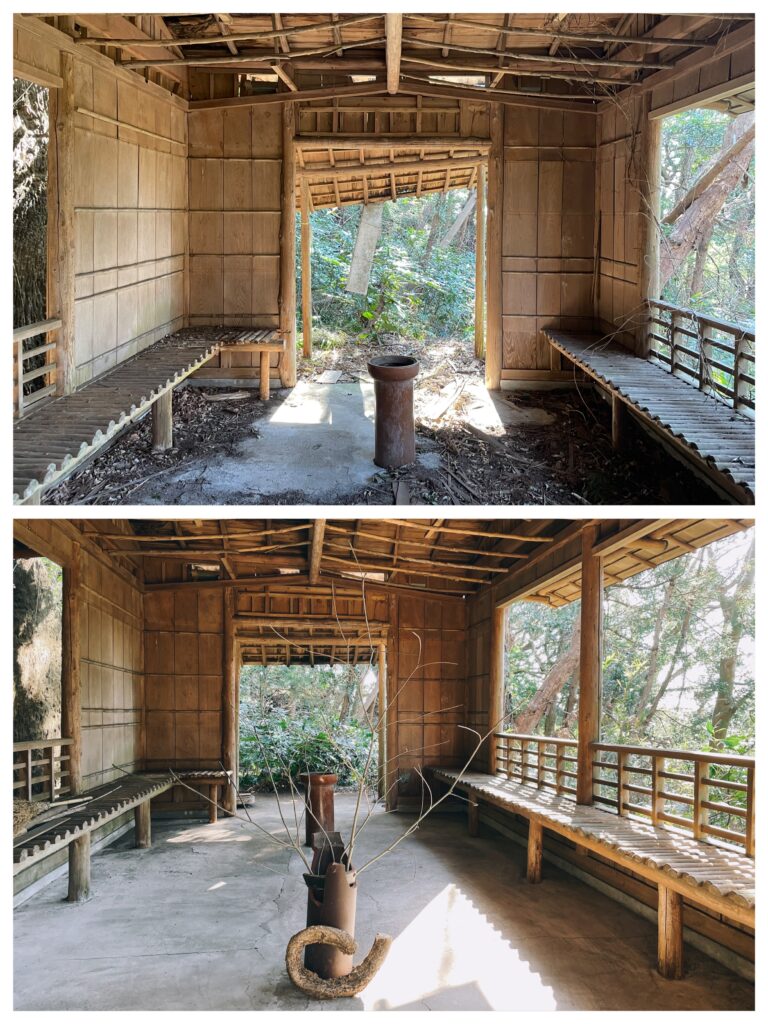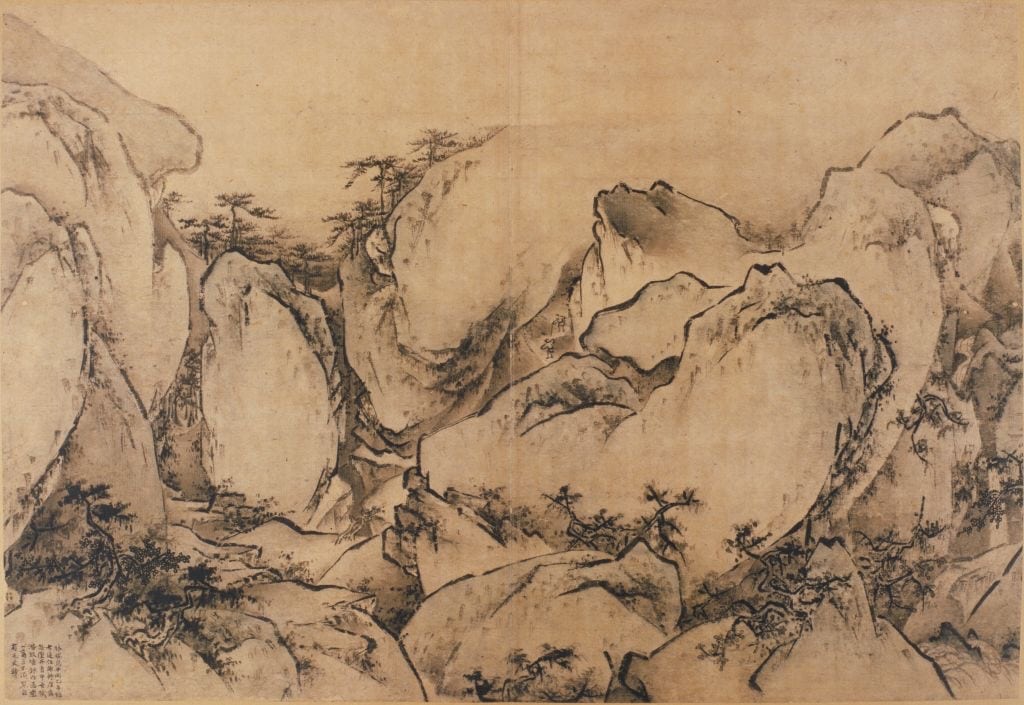野鸟观察

业余时间开始观鸟,在日本叫做“野鸟观察”。长进不多,至今没有成为鉴鸟大拿。不过乐趣倒是多多。看图绘的观鸟手册,读网络上的户外鸟类照片,用肉眼观察鸟类,以及用望远镜观察鸟类,完全是不同的感受。顺序先后的感受也不同。比如某一种鸟或者植物,你已经熟知,然后在野外遇到,和另一只你完全不熟悉的种类,再回去看图甄别,这两种是完全不同的体验。所以于我,自然观察的乐趣不仅仅在于把名字对上,这乐趣又广阔又深邃如宇宙,以至于每当我踏出家门,进入自然空间当中时,冒险便已悄然发生。
尝试记一点零碎的感受,没有图片~
金翅雀——之前听芸窗老师提起过多次,我也查过,印象里不管是哪里的图,都是有点凶悍的小鸟样子,怎被芸窗说得那么可爱。我今天用小镜看到一对做窝的金翅雀才明白了,那圆圆的散着绿光的小毛球,肉粉色的喙,和翅尖闪动的金黄色,怎能令人不心生爱怜。
骨顶鸡——这个我先看到真“鸟”然后查的图册,图册的照片我失望极了,骨顶多么灵动又俏皮的长相,一上照片就变成一个黑脸呆子!今天我看到一只骨顶鸡顶着流水往上游游动,水流太强,它拼命拨水还是停在原地。我简直要被它的执着给打动了。另一次,在八幡宮的池子里,一众针尾鸭,赤颈,绿头鸭大概有三十多只,打闹得欢快,然后只有一只骨顶鸡顶着白脑袋挤在里面和人抢吃的,体型又小,又不是自己人,看客我又为它捏一把汗。不知彼时它是不是也在省思,who am I, why am I here … 后来看别的有更多观鸟经验的说,只有初级观鸟者才会给鸟带入人类情感,与之共情——不过总之,这还是现阶段的我乐趣所在。
北红尾鸲——这是我在开始观鸟以前就看过很多图片的小小鸟,名气不大也很常见。但是每次我看见他,都会怦然心动,仿佛心里有些最柔软的部分被触碰。
鸬鹚——横滨的岩馆旁边经常看见,却从没见过捕鱼。今天在鸭川望见一只大鸬鹚,揪住一条像是鳗鱼还是什么的细长型鱼。那鱼倒很有生命力,不停地扭动,在中午的阳光下面反光成一条扭动的银色链条。这大鸬鹚也不轻松放嘴,在流水中叼着这扭动的银色链条往下游漂流,大概战斗太猛烈,用脚滑水要分心的。这鸬鹚与鱼的交战火热,时不时的这银色链条占了上风滑落到水中,鸬鹚便再潜入水中把那扭动的链条叼出水面。正在我和随线一起感慨这自然界的战斗要多久,以及会如何收场之时,这鸬鹚不知耍了什么戏法,把整个链条塞进了自己的喉咙!它朝天伸直了脖子,费了几番力气好像是吧那条鱼整个咽下去了。我和随线看得目瞪口呆。这时这鸬鹚展开翅膀,又伸直喉咙再咽了一次。随线说“I hope he is okay”,那口气,好像是看见谁贪嘴吃了一块巨型的奶油蛋糕有点噎住了。我说,“多喝点水,涮涮就下去了!”
翠鸟,翠鸟!大名鼎鼎的翠鸟,在网上看到过无数次。在我们所居住的二阶堂山谷里面,大约是有几只翠鸟的,随线近距离看到过一次,回来口口声声描述如何如何漂亮,我羡慕得要命。后来在二阶堂只亲眼看到过两次,离得很远而且也没有带着拿望远镜。那是我人生当中与翠鸟最初的几次相遇,第一印象是怎么如此之小,我又一次被网络照片给误导了。而最近一次在京都植物园的溪流边,我真正通过望远镜能近距离观察到一只翠鸟时,这感觉无法形容,几乎像一道橙色的闪电,她从我们面前闪过——我正跟随线说,北红尾鸲,可声音不对啊?这时她却落在我面前不远的树枝上,我倒吸一口气,立刻抓住望远镜,这不是翠鸟吗。翠鸟!随线按着我的肩让我安静下来,然后我们便肩并肩看着那只翠鸟。借助小镜,我几乎能看清她的呼吸和胸口起伏的羽毛。几秒钟以后,她转动了一下身体,这下是背朝向我们了,我和随线几乎同时发出了一下轻轻的无法克制的惊叹声,她背上的蓝色中间还有一条更亮的蓝色,那一刻我们俩都被她照亮了。